
作者 | 江舟
编辑 | 李固
视频 | 吴振军
自2016年创办科普音频节目《天方烨谈》,尹烨已在喜马拉雅讲生命科学讲了8年。
节目以几乎每天一期的节奏,播出了2821期。
在他看来,科普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跟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情。
“如果今天大家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都是非常简单的猫狗、扭个腰、随便唱两个歌,那么我想大家的时间可能极大程度地给浪费掉了,甚至它容易培养出很多非常极端的思想,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在更新科普内容的同时,尹烨在某平台账号橱窗里也在上架相关书籍,华大的益生菌产品。
面对外界对他的质疑,他也承认自己是在通过科普卖华大的产品。
“我们有非盈利的部分,所以我得理直气壮地卖华大的产品,因为我们还要保证能不断地造血。”
在他看来,生命科学的商业逻辑严谨而漫长,只要货真价实,经得起考验,就无需太多的焦虑。
另一面方面,随着生命科学的推进,尹烨告诉《新浪蜂鸟》自己如今也会怀疑,生命的起源不排除是被其他更高的文明所创造的。
“其实稍微悲观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因为生命科学已经可以尝试设计生命。”
在尹烨看来,能开锁的钥匙一定不在锁上,能告别虚无的方法论,也许最终得求助于哲学。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科普也是再用另一种方式,解释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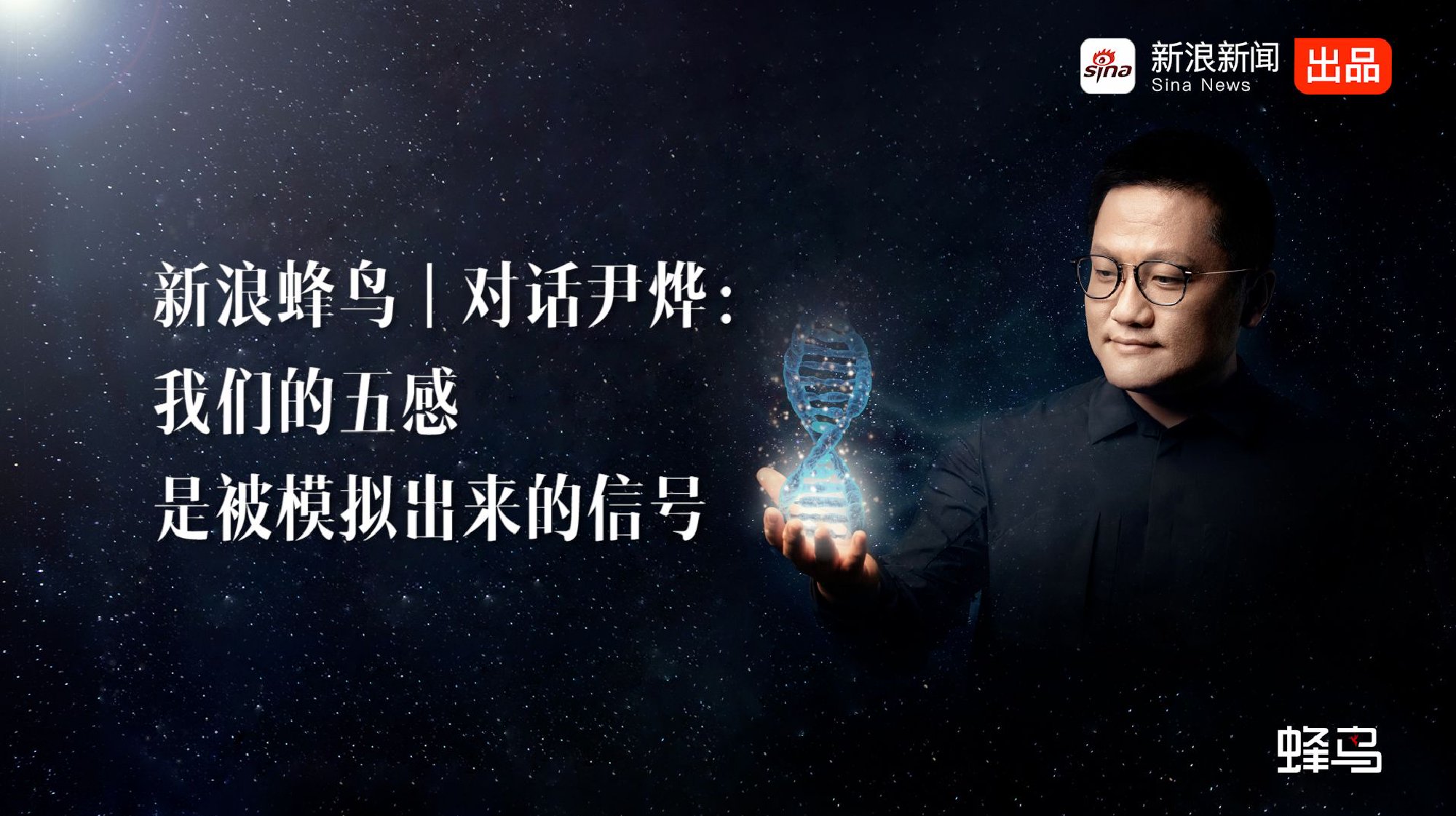 新浪蜂鸟|对话尹烨:我们的五感,是被模拟出来的信号
新浪蜂鸟|对话尹烨:我们的五感,是被模拟出来的信号
《新浪蜂鸟》(以下简称 “蜂鸟”):长久以来做科普,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
尹烨:如果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就要求这样,每一个高新企业,特别是头部的,它要破圈,要能直击人心,要能直接影响到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普可能会对我所在的华大带来更好的美誉度,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华大有什么技术?华大在做哪些科研?华大有什么产品?而不是说我们还要做广告,还要花大量的市场营销费用。
长期来讲,如果你不做,那么谁做呢?大家都等着有一个老鼠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但如果谁都不去挂,生命科学最后怎么起来呢?我一直做科普,始终所笃信的: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科普也是。如果今天大家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都是非常简单的,猫狗、扭个腰、随便唱两个歌,那么我想大家的时间可能极大程度地给浪费掉了,甚至容易培养出很多非常极端的思想,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我们的肠道有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的总量要比人类所有细胞的总量多3至10倍。我们在肠道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病毒,是专门以吃这些细菌为生的,这些病毒的量又是刚才讲到细菌量的10倍或者更多,所以每天早晨我们只要排一次大便,马桶里面就会被排泄超过11万种病毒,它们都是肠道的共生病毒。这就是我说的,这对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是ABC的事情。但如果这些ABC的问题不去解释,今天相当比例的人类并不比显微镜发明前的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所进步。
蜂鸟:基因和Sora或ChatGPT如何做到交汇?结合的原因是什么?
尹烨:互联网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信息平权的问题。现在信息茧房太多了,我们现在的算法都是推荐搜索,这个需要混入随机的破解搜索,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无限地被自己原来好像就相信的观点强化,这实际上会让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出大量的人工智障。
人工智能带来的(另)一个可能是知识的平权,甚至未来是智力的平权。所以,实际上是互联网在高度发达了以后,由于数据、算法、算力,各个点都在突破它(人工智能),使得它开始出现了“智能”,或者说出现了一部分我们认为的“感知”,甚至是到了“认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有一天它会有“觉知”,就是“硅基会不会真的有生命?”。生命科学有多个点上,跟这件事情都是高度相关的。
其实生命是特别需要用大语言模型去解释的。对于生命的语言来讲,它的数据是不够的,其实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基因数据,现在估了一下,全世界的覆盖率仅有万分之3。电我们90%的人可以用,互联网差不多普及到60%到65%了,然而人的基因数据只有万分之3,这其实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说明书,所以基因测序的未来是个星辰大海
蜂鸟:在人工智能面前,很多东西都有一种虚无感,生命科学会这样吗?未来有人工智能了,我们的生命还像以前那么宝贵吗?
尹烨:历史上科技颠覆的东西多了去了。汽车的发明就取代了马车,但是,那一批愿意当司机的马车夫,他们就拥抱了科技的变化,而不是天天到街上去游行,反对汽车的发明。技术难道会等你吗?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小伙伴,在哪个行业,都会有被颠覆的可能。
我一直在讲人工智能时代比拼的是什么?它比拼的是想象力,比拼的是创造力,比拼的是可以跳出这个盒子去思考问题,能不能做出没有人想过的东西。什么是宇宙的边界?人类的思维边界。所有人类能想象到所有的事情就是宇宙的边界,不管符不符合科学,即使它是唯心的,即使它是玄幻。我们怎么可能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桎梏当中,而不敢大胆地去蹦一下?
今天的基因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我们才需要大量的去产出基因信息。就像你今天在华大的总部,看到了我们的测序仪。华大的测序是领先全球的,领先美国,那么只有当我们有更多的数据产生出来,才能基于这些数据发生“涌现”。这就是所谓的标度律,类似于加显卡就能产生超级算力,超级算力就可能涌现出我们所谓的智能或觉知。我们人也一样,通过大量的测序,就可能从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若干个“噪音”当中跳出信号,告诉你这些知识。慢慢地还会从弱相关到强相关,甚至到因果,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这个领域叫“没钱挖数据,有钱多测序”,不要去猜。
蜂鸟: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基因数据库是个什么样的分享状态?
尹烨:在过去,我们理解成是一个处于相对共享的状态。这个地球上有几个大的基因库,美国有一家叫NCBI,是它的国立生物信息中心;欧洲有一家叫EBI,是欧洲的生物信息中心,在英国德国都有布局;日本有一家叫DDBJ,也是它国立的一个基因库;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数据库,比如说深圳国家基因库,这是由华大代运营的,比如说中科院有一个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它们彼此之间一直都处于共享状态。
当然分享的规矩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是不能分享原始数据,只能分享位点频率数据。但是就在去年,我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应该感谢英国直接公布了50万人的全基因组数据,包括各种各样的表型数据,每天运动的数据,甚至一部分医疗的信息。但他们特别强调的是要保护个人隐私。
所以到这一刻,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让人类真的去共享和使用这些数据,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或者说,哪怕英美都对中国进行数据关闭了,中国在境内也应该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群数据库,才能有比较优势,才能够去支撑我们未来的精准医学和健康的创新发展。
蜂鸟:基因共享的意义是?
尹烨:任何的罕见病都是有发病率的。比如说拉脱维亚,我们假设它就是100万人口,就算千分之10的出生率,每一年就是有1万个新生孩子,如果这个罕见病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一,那么10年可能才遇到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拉脱维亚做某个罕见病的研究,10年可能才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个体。
但如果从全世界去看,我们有80亿人,每一年大概9000万个孩子出生,再用十万分之一这样的比例去算,一年就可能生出差不多900个罕见病孩子。这900个孩子如果都做了基因测序,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罕见病可能出现的基因位点,这个基因位点就可以加入到孕前或产前的基因检测中,能够帮助父母进行预防。
所以如果大家都不共享数据,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某个罕见病它的一般性规律是什么,但如果大家保护好隐私一起共享,也许只用一年这件事就能解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这些数据,实际上就是应该彼此共享,才能够极大地推进我们科学的发展,医学的发展,社会学的发展。
蜂鸟:中国在基因数据共享上跟国外是有怎样的差距?
尹烨: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差距。中国如果散着来算,我们也有上百万份人的基因数据。比如A医院、b医院,a城市、b城市,a机构、b机构,但是彼此之间是有壁垒的。实际上,如果从整个人口基数的角度来看,全世界能够查到的黄种人的数据是最少的,而且绝大部分数据来自于新加坡。真正中国人的全基因组数据,经过批准公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查到的只有几百个。
中国的基因数据,是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来管理,这是国务院的一个法律法规。中国对人力资源的保护是相对严格的,所以必须要经过对应的批准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共享。
蜂鸟:生命科学的商业逻辑是怎样的?
尹烨: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看到一个产业出来,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有了利润再回报给科技发现,一般来讲一个学科是这么循环的。医学领域即使你知道青蒿素能降低疟疾感染死亡率,你还要回到科学发现,去搞清楚为什么?它的药理是什么?毒理是什么?临床在哪里?生命科学领域是不允许发现直接到发展的,必须回到发明,这就是它的周期,就是长。
我们今天的医学或者是生命科学,不允许直接演绎,我们只认归纳,即使你演绎的是对的,我也必须在真实世界当中找到这个证据再来用。这两件事情都决定了我们需要有更长的耐心来看这一个过程的闭环。
所以,其实能做好科研的组织很多,能做好产业的也很多,同时能做好科研产业,还有教育还有国际化的,华大算一个,而且很难找对标的,没有一个其他的组织。我们自己都不能叫一家公司,因为确实有非盈利的部分,我们是从科学从教育到技术一直到产业全部做完。而且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还要保证我们自己能不断地造血。
其实在过去,华大To B、To G都做了好多的努力,我们跟政府一起推公共卫生的一些民生项目,做一些普筛,预防一些遗传病,预防一些中晚期恶性肿瘤的发生;我们还跟研究所跟大学跟药厂,特别是跟医疗机构相合作,这是To B。
To C在哪?我们需要有一个抓手,其实我的科普就是To C。但这就好比是一个空间,科普更加倾向于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面。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能落地。益生菌是其中一个我们看得见的,而且从全世界来看,华大是原研者,是第一批的开创者,所以做这个东西也算是根正苗红。从对肠道菌群的研究,到益生菌这样一个闭环,它背后是大的一套这样的产业逻辑。
今天你看到了好多益生菌的牌子,它是买的进口的原料,自己做了一些包装,它更趋向于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我们希望从根上开始研究。
我要从菌株开始追溯,要来自于中国人的健康的肠道,这些菌株经过我们全基因组的测序,确保它的真实有效,同时申请专利,还要经过层层的工艺筛选才能到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叫“了不起的民族菌”。
蜂鸟:你的教育观是什么样的?假如一个6岁的孩子坐在你面前,你如何让他来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尹烨:但凡能讲出来的东西就没意思了,我会带他去大自然。带他看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虫?见天地,见众生,见自然,生命是觉知的,生命可以被教授,但绝不能被简单的copy。我讲出来的他没见过,但我带他到自然当中去,那个东西就会让他直接入迷了。
现在我们都强调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但是五育并举要求的是群体,不能要求个人。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能说我们德智体美劳都好吗?以我举例,我美育就不怎么行,我又不画画,我们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在追求一个完人的时候,他反倒可能一个事都干不好。
我们太喜欢给出一个理想当中的模型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应该对群体要求的,我们却具象化,应该很具象化的,我们有时候又群体化,这其实是一个蛮扭的事情。
所以,德智体美劳应该是鼓励每个孩子努力的方向,但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全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他文艺并举。还是我刚才说的,要让他在自然当中去感悟神奇生命,到田野当中去感受盎然生机,德智体美劳就都感受到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美育;认识生物多样性,他天然就会很好地去学习,这是智育;他发现了万物生光辉,每一个小草上都有一个露珠,自然界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配合,尽管它们也会有竞争,但竞争是以后确定的,今天我看到的是一种和谐的配合,这是德育;等他走累了,他可能挖个坑、搭个帐篷,这就是劳育。
我所希望的教育,就是能够把这个人教成一个热爱生活、充满自信的人,而不是活在一个被别人评价的世界里面。
其实我是被训练出来的,有点像ChatGPT。4岁以前我被父母喂了大量的语料,然后我就不断地被反复强化,去听这些故事,去产生各种各样神经元的连接,去学习他们的语音语调和表达。实际上,人的语言能力是天然存在的,这也是人为什么能够演化为人类的根本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爹妈多花时间在6岁以前陪孩子,是会受益终身的。
蜂鸟:如果人类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生命科学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吗?
尹烨:其实稍微悲观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被更高等的生命设计出来的,因为生命科学已经可以尝试设计生命。去年我们设计的酵母,是第一个全部的染色体和遗传物质都由人类设置的真核生物。那个细胞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但它里面的程序被我们重新改了一遍。
您的问题对我来讲非常难以回答的就是在于,我连我们今天的五感六通,都不知道是不是虚幻的。今天的脑机接口已经存在了,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哪怕是意,我们这些色声香味,它可能都只是一个模拟的神经信号,电信号、化学信号或者是量子信号,我们今天越研究脑科学越觉得是这个样子。
你能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你眼睛的分辨率就是70微米,你只能看到可见光,你看不到我的骨头,因为你不是紫外。我们看到的,都是所谓的大脑想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元宇宙”而已。
能够打开锁的钥匙一定不在锁上,我们可能要用哲学去解开科学的问题。说起来比较虚,但是我一直讲一句话,因为我是做生命科学的,我深知生命就是一组代码,我们人类的程序代码量跟猫跟狗跟猪都差不多,但是人类这个代码的组合,它涌现出了爱。
我们人脑真正了不起的是,它可以神经元重塑,其他物种没有这个本事。人脑的可塑性是最宝贵的东西。守脑如玉,比守身如玉,有的时候更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辩证地去看,不去极端地回答这件事情行还是不行。你问我最后什么能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我可能说是爱,只有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