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浪蜂鸟 | 对话田雨:我有小富即安的一面
新浪蜂鸟 | 对话田雨:我有小富即安的一面
作者 | 张子悦
编辑 | 李固
视频|徐准、吴振军、王爱琳(实习)
《新浪蜂鸟》见到田雨,是在《庆余年2》收官的次日。
和一些喜剧演员一样,镜头之外的田雨语速缓慢,嗓音低沉。
面对提问,他很少立刻回答,认真聆听后,通常会先进行短暂的思考。
像是有些问题,已经很久没有人向他问起。
关于“王启年”的话题,是他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刻。
在现场寒暄时,有人谈起“轻功了得”,田雨笑着说,那是他现场提出的意见。“我说我这有轻功,干嘛要骑马。”
对于《庆余年2》的创作团队,他都会冠以“老师”。“猫腻老师、王倦老师……”
他说自己当下提供的是“情绪价值”。“有时会碰上一些人,他们说创造了这么多欢乐的角色,很感谢我。”
但他记得在中戏时老师的教诲,和最喜欢的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
“他就完全方法派,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拍戏。老婆做导演,他就帮忙做一堆布景之类的……”他仍关注着这位唯一的三座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拥有者。
他告诉《新浪蜂鸟》,现在很多关于表演的经验和期待,都被他放在了一个随身的箱子里。
“你会随身带着它,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于是他也像是一个带着隐形皮箱的中年人。
如果与环境不符,他会把拎箱的那一只手,稍作调整,微笑着伸出,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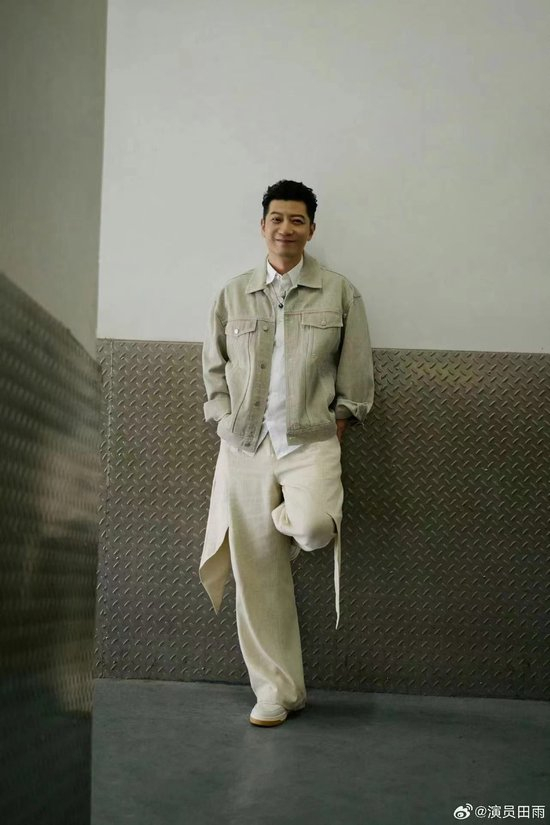
提供情绪价值的演员
新剧拍摄结束后,田雨立马从片场返回了位于北京东边的工作室,准备接下来的采访和直播。
收工比想象中早,所以给《新浪蜂鸟》的时间也多了半个小时。
等这部剧拍完,气温接近40度的时候,他想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投入下一部电影的拍摄中。
随着《庆余年》等剧的走红,以及白玉兰最佳男配角的加持,田雨越来越被更多人熟知,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黄金配角”。
相比于自己年轻时的作品,田雨感受到最直观的变化是剧本的差异。
他谈到了一些区别,“那会的剧本更注重文学性,现在更多看大家怎么能接受,能提供怎样的情绪价值。”
田雨充分理解变化的原因。
“现在观众太聪明了,很多道理大家都懂,观众更在乎是否能与角色产生共鸣,这个对他来说更重要。”
出演过许多喜剧角色后,有陌生人遇到田雨时会说:“你这么多年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欢乐的角色,很感谢你。”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多点欢乐挺重要的。”田雨认真地说道。
《庆余年2》播出后,有网友评论称王启年是“大庆人形高铁”“狐狐饲养员”,田雨看到了这些留言,觉得很有意思,还在告别博文中特意提到了这些评论。
“弹幕太好玩了,我觉得那(也)是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说这话时,田雨露出了笑容。
北京与矿区的孩子
1975年,田雨出生在北京妇产医院,关于名字,他说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我哥那会儿学雷锋就叫田雷,完了先打雷后下雨,然后叫田雨,很简单。”
童年时期,田雨跟随姥姥姥爷在北京度过。姥姥家是一处只有9平米大的平房,位于平安大街和护国寺之间的胡同里,紧挨着人民剧场。
虽然条件不算优渥,但在这里,田雨接受了最初的艺术启蒙。
人民剧场经常上演京剧,京剧演员在后台开嗓的声音、华丽的戏服,都给幼年的田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姥爷那会也看京剧,晚上洗脚盆里一双大脚丫、一双小脚丫,我俩就对着一起听收音机里的京剧。”
1976年,唐山大地震爆发,距离仅数百公里的北京震感强烈。
不久后,北京大路边见缝插针地搭起了简易的棚户——“地震棚”,屋里的床位也同样被改造,特点是床铺离地很高,平房里的上下铺。
借着蚊帐或床帘,田雨和哥哥披两个毛巾就开始在棚里演绎各种才子、英雄。他说,蚊帐被拉开的时候,就像幕布一样。
8岁之后,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田雨和哥哥来到河北承德上学。
父亲大学毕业后在平安堡煤矿工作,家就安在铁道边的一处平房内。
北京到承德的绿皮火车会经过那个位置,他甚至可以透过车窗,看到自家的房子。
矿区的孩子和北京完全不同,有一种粗旷的劲儿。
田雨记得,矿区有一种废弃的大电池,“流汤的那种”。他和伙伴把电池砸开,抽出里面的碳芯,用它在土墙上写字画画。
电影同样走进过他的生活。上小学时,电影《成吉思汗》在避暑山庄拍摄,同学之间传话,说有剧组去了附近的小学里选演员。
“但那会儿,还是没想过要做演员。”
身体稍微长高了一点儿,田雨就被业余体校教练选中,练习了一阵柔道。
田雨还记得教练说他天赋很好,说好好练能有机会去亚运会。但一次受伤之后,父母关闭了他的体育梦。
那个时期,日常在矿区生活、寒暑假来北京玩耍的田雨,觉得未来充满了机会。
“就爱琢磨,想的事情特多。”
上高中时,他有一段时间对修理汽车特别着迷,甚至想辍学去修车,“觉得修车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后来又想过去当警察。
随着1994年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上映,此前赵宝刚导演的《编辑部的故事》播出,田雨喜欢里面的演员,开始觉得演戏有意思。
那时,表姐在中国音乐学院学钢琴,一次闲聊中,她建议田雨去考中戏、电影学院学表演,打开了他的一扇窗。
虽然家里无任何文艺背景,父母还是支持了田雨的决定。一家人交谈过一次后,父母支持田雨先上一个表演培训班。
到报考时,因为同时报了中戏、北影、上戏,父母还给他出了去上海考试的路费。
“那个时间段我就恰好想干这个事儿,也挺努力的。父母也支持,可能他们本身是搞教育的,就希望我们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在田雨看来,那时的他想法简单,大学的选择与未来和责任无关,只想投身一个自己觉得有趣的行业。
“那会觉得干什么都挺有意思,考不上中戏可能就修车去了。”
从未想过要当明星
1995年,田雨顺利考上了中戏。他记得表演系报名有几千人,只录取20人。
凭借一场讽刺办公室政治的即兴表演,田雨从中脱颖而出。
提及这场表演的来源,田雨说:“那会陆续好多影视作品上都有这样的故事,我父母在承德石油学校当老师,有办公室的环境。小时候在学校里勤工俭学,帮图书馆对对书,一天给几毛钱,我对办公室的环境也有所了解。”
同一时间,中国电影市场正在迎来变化。
1993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电影市场化元年”。《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取消了中影公司对国产故事片的“统购统销”,改由制片厂直接面向电影市场发行放映。
从此,中国电影业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当年,《霸王别姬》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成为首部获此奖项的中国影片。算是为时代画下了精彩的句点。
之后,《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年)和《甲方乙方》(1997年)进一步打开了年轻人的电影市场,电影市场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游戏规则。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戏依然保留着自己的风骨,对于市场和公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例如在招生上,也遵循“舞台”的规则,选择自己的学生。
田雨说:“老师招我们这班学生时,是要搭成一台大戏的,每个人的特点和型都不一样。我一开始是按武生的形象招进来的,后来定位逐渐变成了老生。”
“剧本逼着你想更多事儿,20岁的人去体会60、70岁人的心理状态,始终在够一些东西。”
田雨特别记得,徐晓钟老师讲戏时一秒入戏的情景,前一秒一个状态,后一秒进入角色,突然就变化了模样,让田雨觉得神奇。
“那会学到了好多东西,我特别感兴趣、特别痴迷。”
学校要求大一就进行汇报演出,他经常筹备小剧场,和同学讨论怎么把人物演得有意思。
小剧场的空间很小,观众和演员的距离非常近,基本是面对面访谈的距离。有时演员从台上扔一个包,转头就发现挂观众脖子上了,只得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拿下来,继续表演。
除了舞台剧,他也尝试过外出接戏,但命运使然,在另一个道场,他当时并没收获太多橄榄枝。大三时,有个导演把全班人都选走拍电视剧了,但老师唯独留下了他。
“当时也有特别着急找我,我也很想去的,但就把我摁下了,不让我出去。”
在田雨的记忆中,梁伯龙是很新潮的老师,也有传统的一面。他早晨会起晨功,田雨几乎是4年里起晨功起得最勤的,所以基本上每天早上他们都能见面。
梁伯龙不建议田雨出去拍戏,“你不能去(拍电视剧),那些东西很简单,你好好把大戏演好,出去闭着眼睛都能演。”
一次班会上,梁伯龙拿田雨举例,“你们都出去拍电视剧,你看田雨没出去拍吧?这样我们呈现一台大戏,多好啊,是不是比你们出去挣钱有意义?”
《地质师》《仲夏夜之梦》《热线电话》。。。。。。田雨的校园时光多数都花在了舞台剧上。
毕业时的四台大戏,田雨一个人参加了三台。邓超在综艺里曾透露,“田哥在大学时代就是我们的楷模。”
此时,舞台之外,现实差异已开始显现。同班同学里,夏雨在上大学前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是当时威尼斯电影节最年轻的影帝。
和他们相比,田雨像是只把表演当成了学车、练柔道一样的手艺,和成为大明星无关。
在校期间,他曾碰上巩俐回校探望老师,那时巩俐已凭借《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屡获大奖,但田雨只是远远地看着。“就是仰慕的眼光,完全没想过,我以后要成为大腕什么的。”
类似《霸王别姬》里,小癞子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角儿啊?”的奢望,
田雨说自己从未有过。“成角、明星,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踏踏实实演自己的戏……我可能太随遇而安,老觉得生活得慢慢走,我没较那么大劲后悔。”
通常来说,演员并不是一个令人踏实的职业,它具有明显的“赢家通吃”的属性,要么成名拥有一切,要么无名一路颠沛。
竞争通常在学校里就展开,为出名费尽心思,焦虑无处不在。
但田雨身上似乎有一种安全感,让他有底气不争不抢。
谈到这份安全感的来源,田雨否认因为是北京孩子,“犯不着,就9平米,那么大点地方。”
但他也说不清自己的安全感来自何处,只记得两个因拍戏遇到的场景。
一个是上学时,他帮舞美系的同学通宵做布景,完成后爬到楼顶看日出,太阳初升,散发着像舞台一样的光,潜藏在光下的城市,很像布景。
另一个是人生首部电影《真心》到新疆取景,蓝天、白云、戈壁滩、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帕米尔高原上的美景震撼了他。
“我的那个点可能不是非要钻营拍一个什么戏,我觉得那些东西给我的人生营养可能比拍那部戏还要重要。”
在《真心》转景间隙,田雨在招待所的院子里跑步,前辈鲍国安提醒他,高原上注意身体。那时已有轻微高反的田雨,还是坚持一圈一圈地跑。
“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有精力耗不干净。”
贫穷的堂·吉诃德
成角的急切和演戏的疲累没能耗干田雨,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他。
上学时,排戏碰上学校宿舍装修,田雨就住在排练场里。
正值夏日,排练场没有空调,他就开着窗,把布景的硬木板搭上,铺开凉席当床。
到了饭点,没有食堂,田雨会跑到菜市场买两张饼,然后去当时最好的商场,被誉为首家中外合资的百货商场——复兴门百盛里的日料店领几包免费酱油,就着酱油把饼吃了。
此前的采访中,他透露,24岁在长春拍戏时,他总是一个人到处走,或者待在宾馆看DVD,觉得很孤独。
洗衣服的时候他会想,自己在这干嘛?北京有那么多亲戚朋友,自己为什么做这个?
在演员黄金的27岁到30岁,田雨是在迷茫中度过的。他渴望创作人物,但一直没有工作的机会,只能跑跑龙套。工资收入微薄,生活上也捉襟见肘。
当时,田雨住在五棵松,每天坐地铁去剧院排练。有一次,组里一个老演员开着一辆切诺基顺路捎了他一段,他才发现原来地面那么有趣。
有一年生日,田雨在剧组帮人串两场戏,服装组给了他一件带窟窿的毛衣,胳膊都露在外面。
“我心里当时可难受了,过生日给我穿一破衣服,倍儿难受。大冬天拍到凌晨一两点,回宿舍只能跳墙进去,都熄灯了,黑灯瞎火的,那时也没有卸妆油,拿张纸擦擦脸,爬到床上就睡了。”
为了抵抗现实带来的不如意,田雨在那段无名的时光看了大量的电影,一天四五部,跟朋友在家里拉黑泽明的片子,反复看。
“看了那么多好电影,你知道好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才会奔着那个目标去。”田雨说。
现在回顾那段时期,田雨不喜欢被说成忍耐,更愿意形容成“积累”。
他喜欢摩根·弗里曼的一句话,“我的演艺生涯从30岁开始,至今一直在不断积累。表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从中你能体会到很多东西。生活不会向你许诺什么,尤其不会向你许诺成功,但是它会给你挣扎、痛苦和煎熬的过程。我的幸运在于,在此之后我获得了成功。”
这段话于2011年在田雨的微博出现过,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到何时才能获得成功。
走下舞台
2015年,《夏洛特烦恼》首映礼在政协礼堂举办,田雨很激动,发微博说:“小时候在政协礼堂看过电影,今天没想到会在这块银幕上出现我的影子。”
电影里,田雨饰演王老师,一个贪财势利但又对学生负责的角色。他曾经表示,“一开始(接到角色)是拒绝的,因为父母都是人民教师,所以老师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为人师表,我不能理解这个角色,但跟导演聊过之后才发现王老师是极具戏剧色彩的人物,应该赋予他多层面的含义。”
《夏洛特烦恼》总票房突破14亿,当时仅次于《捉妖记》和《港囧》。凭借在电影中的搞笑表演,田雨开始为大众所知。
在此之前,《大丈夫》《钢的琴》已经让他有了一定的名气基础。之后,《虎妈猫爸》《恋爱先生》,让他在热播剧中持续打开公众知名度。
2019年,《庆余年》出现,电视剧和王启年一角都爆火,田雨借此获得了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
此前,虽然他曾凭话剧《肖邦》获得文化部优秀表演奖,但从业20年,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重量级影视奖项。
此后,他不仅在热播剧中频频现身,例如《流金岁月》的范金刚、《精英律师》的何赛、《纵有疾风起》的沙舟,还和张艺谋合作《坚如磐石》,和韩寒合作《飞驰人生》,和文牧野拍《奇迹·笨小孩》,和陈凯歌拍《妖猫传》,正式进入多点开花、持续走红的状态。
2020年父亲节,他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背影照片,配文“这就是爸爸”。
背上有他饰演过的角色剧照,最显眼的五张依次是《庆余年》的王启年、《精英律师》的何赛、《那一夜,我给你开过车》的李渤、《来电狂响》的文伯、《飞驰人生》的教练。
拥抱变化
对于变化,田雨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拥抱的。
“时代的变化是正常的,不可能不变化,我们也没法还活在以前,你左右不了这个事。”
“其实你也说不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就像纸质图书,也许将来就是没有了,没办法,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再继续……”
田雨说,这些不会困扰他,和早期入行相比,虽然氛围上有改变,但对他而言,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
“还是原来老师和家里人要求我们的那些,认认真真去做事情。你逐渐积累了经验,慢慢去把它们呈现出来,然后跟大家伙交流,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好的。”
腾讯视频首页《庆余年2》的海报中,张若昀、李沁、吴刚或正襟危坐、或抬头微笑,形象都是美丽帅气的,只有田雨在左边举着酒壶、表情诙谐夸张,和旁边三个人格格不入。
有粉丝为他打抱不平,但田雨并不觉得委屈。
“我们的最高宗旨是要把戏演好,完成剧作本身需要的人物,帮助导演完成自己那部分工作。”
田雨很感谢《庆余年》,曾经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剧组的创作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戏,彼此之间都很亲近。
他也喜欢王启年这个人物,在采访中将王启年比作“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合体”,表面是世俗的桑丘,内心住了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
“他心里有自己的骄傲和坚守,但不愿意嘴上把这些听上去高大上的东西说出来。”
这些年,凭借喜剧角色打入市场后,有一种声音称田雨的戏路固化了,似乎被打上了某种标签。对于这样的看法,田雨直接说自己没有非要从某种标签逃出去的执念,随缘。
他曾反复表示,“不论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几乎还是在这个大框架中,真的逃不出去。很多东西是逃不出去的,起码我认为我是逃不出去的。”
田雨认为,角色无分大小,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满意当下的状态
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田雨最放松的两个时刻,一个是聊童年,另一个是聊古建筑和博物馆。这时他会放下撸起的袖子,张开交叉的双腿,眼里带着光,脸上浮现出笑容。
浏览他2011年-2012年的微博,发现有古典音乐、博物馆、哲学、摄影……多元的趣味一方面来源于家庭,受父母影响,他小时候曾在书架上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另一方面,这些别人眼中的“无用之物”,对田雨而言自有独特之处。
几天前,他去门头沟的一个村落看到一处建筑,立刻就说像明代的。村里的老先生证实了他的猜测,说房子属于明朝一个状元。田雨又说,按这房子的制式,应该不止眼前的小院,前后应该还有建筑,后来了解到确实如此,因为山体滑坡和人为改造,前后建筑都消失了。
了解这些让田雨觉得兴奋,“一个是拍历史剧,演员需要了解他们过去住是怎么样的,吃什么东西,穿戴什么。另一个,我觉得人得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现在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此前,他对媒体说过,东西比人可靠,它一直没什么变化,不会给你任何伤害。你可以想象它背后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审美的能力。
在剧组时,田雨常带一尊达摩,有基座也有小香炉,往房间一摆。还有古人用的磬,声音虽然不清脆,但听一听古代的声音,想一想当时人们的心境,他觉得心就容易安静下来。
综艺《哈哈哈哈哈》曾到景德镇拍摄,正巧碰上开窑,本不在日程里,但田雨特地向节目组申请了半天时间专门观摩,亲手从窑里往上拿瓷器,第一次发现瓷器刚从窑里出来时还会叭叭作响。
这些瞬间让他感慨当演员的好,“做演员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伸开日常生活的触角,你所学、所感兴趣、所得的任何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有营养的。”
《庆余年2》播出后,出现了对王启年女儿王霸小名的各种说法,田雨有理有据地告诉我们:
“王霸二字来源于一方汉印,这两个字就代表着霸道。我觉得王霸不是一个烂梗,这是王启年保护家人的一种方式。像对外宣称妻子厉害一样,给女儿取这么一个霸气的名字,也是希望她在外别被欺负了。”
喜感的角色之外,田雨更像一个内敛沉静的传统艺术家,他在解决角色提出的问题中获得快乐,把这些有用的和无用的都看作“美好”。
“我对它感兴趣,就希望投入进去。”
田雨觉得,当下的自己是最舒适的状态。
“一直拍,就挺开心的。你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会学很多东西,每一个人物的成长,包括和观众之间的交流,都是美好的。”
最近他公开表达喜欢的一组照片,是在菜市场拍摄的。照片中,田雨或坐在街边的早餐铺,或脚踏鱼缸、躺在摇椅上,又或是站在塑料水果筐边。
将近知天命之年,当《新浪蜂鸟》问及人生理想的一面,田雨的回答显得有些朴素。
“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地过着每一天。”
带着理想的箱子
最近,田雨在B站上偶然刷到了自己过去演《钦差大臣》的片段,惊叹于当年竟然能完整说这么长一段台词。
拍戏25年,田雨从京剧认识舞台,从90年代的经典影视作品喜欢上表演,他感受过舞台,有过生活经历,但时代在变化,市场也在变大。
田雨看到并接受了这些转变,但他依然记得演员前辈对他说过的话,也记得自己的偶像。
这些年,田雨一直在尝试一些正剧和小成本的艺术电影。虽然没有喜剧角色传播范围广,但他并不在意,“没被注意到也没关系,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做。”
表演时,他惯常使用的方法是人艺创始人焦菊隐提出的“心象说”,要求演员通过认真阅读剧本和深入现实生活,在心中形成角色,然后寻求角色的行为动机和表现方式。比如王启年心痛地从鞋底拿出藏好的银票,就是参考了葛朗台。
田雨的偶像是丹尼尔·戴·刘易斯,希望能像他那样花一两年准备一个角色,同时又有一整个团队帮助演员蜕变。
他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试,但到现在,他觉得自己还没完全做到专业化和职业化,离真正的体验还差得远。
现在,他说:“我可能拼不过他了。”
不过,他一直记得行业内的老先生对他说的两句话。
一句是,演员越往后处理人物,越是演自己的理解。
“一个回头、一个停顿、一个眼神,演员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这不是教的。演员得幻化出一个自我附着在人物身上,或者发自内心地想通过一个人物把自己的部分认知传递给观众或对手演员,才能做到。”
“你要积累多年,又要把它变得不一样,避免重复,这事真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另一句是,演员有时一辈子就在等一个角色,方方面面都和自己契合的那个角色。
老先生曾对田雨描述等到的感觉,“很短暂,又很幸福。”
“王启年算那个角色吗?”《新浪蜂鸟》问。
田雨思忖了很久:“我觉得还好,可以通过他表达很多东西,让观众认识你。”
“理想还在箱子里,对吗?”《新浪蜂鸟》问。
“对,理想召唤所有人,只要能呈现出一点点就可以了。”




